


天冷,不太愿写了,但是做事得有始有终,这是我常常训导女儿的,于是我又戴上手套接着开始了,呵呵,只是速度较慢!
记得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好象是初夏吧(大凡是夏天我才会到河边走动得较多),我起了个大早,把我的一个蚊帐布的小网放在河中,又在小网边上放了一个大点的网,于是我就开始了等待稳坐钓鱼台后的收获,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心里不停地在嘀咕着:跑网中央去,跑网中央去,近点,再近点······,终于我猛地一拉网,呵呵,小有成就,几条手指般的扁鱼在那挣扎跳跃,我开心地把它们放进我的小水桶,然后又开始下网了,由于天气比较早,鱼儿好像也格外的多,景色更是不用提了,俨一副:“烟笼夏水雾笼沙,孩提不知勤学早,隔江犹垂河中鱼”,但就在此时,我发现在那河近九十度拐弯处来了许多的木筏,其实,那木筏在蜀水河中也不是经常有的,只是隔一断的时间才有,还是在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会常有,好像后来的记忆中就没有了,可能是树木砍伐得没有什么了,再则就是交通发达了,人们不太走水路了,总之,看到那悠长悠长的木筏后,我有些激动,要知道,可能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那么壮观的木筏长队了,它们好像有五路,一路有一个舵,那种舵,就是那种抗战电影里的杀鬼子用的刺刀状,只是放大了无数倍,如机关枪一般驾在正前方,可以用手向左向右扳动,我和弟弟常常乘没有人在的时候摇得嘎吱嘎吱响,很好玩,只是我不明白这些掌舵人的性子是如何磨就的,这河水流动得如此缓慢,他们这样放木筏,也不知从目的地漂流了多久,不过,到了我们八一八,也就是这条的河的末段了,也就意味着他们马上要回家见到家人了,所以,我常常很少在八一八河段的木筏上看到放阀的人,可能他们按奈不住马上就要回家的喜悦,上我们八一八的商店去买东西了,也就是备礼品给家人,想给家人个惊喜吧。
看到那木筏我已经没有心思捕鱼了。
那木筏远远望去,好象是座浮桥,一下子把平日里清澈宽敞的河面平铺得严严实实,宛如五条水龙盘据在蜀水河。我估摸着那木筏到我家门口可能还要一阵子,我想大概中午能到吧,于是我就开始憧憬着那木筏来到后的情景:我和弟弟可以从木筏的这头走到河对面,更可以到河对岸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野果或者有没有那种大竹笋,再则我们可以看看木筏的木头间隙中有没有搁浅的鱼儿,还能再摇一摇那大舵,还有那龟,那久违的小龟,总之,我仿佛已经在那木筏上徜徉了······
到了中午,一放学,我撒腿就往河边走,只见那木筏的一部份已经到了我家门口的河边了,而我那捕鱼的网已经给挤到了河边边了,已经没有办法搁置了,于是我就回家拿了丝网,来了个吆喝捕鱼,我站在木筏上,弟弟在河边,我把网布成弯月形,等鱼儿进了我布下的阵以后,便和弟弟同时跺脚吆喝,那鱼一受惊吓,不辨方向,四下里乱窜,全往我那网上钻,那一网,我捕到了十来条大的川条鱼,晚上家里美美地吃了一顿。但是这个方法第二次再试时便不管用了,我想鱼儿可能也是有智商的,它们再也不靠近我和弟弟所布网的水域,我看这招不灵了,只好把网往岸上一扔,准备往木筏深处走去,想到河对面去猎猎奇,可是当我走了一会时,发现了木筏上的一个小竹棚,它们是拱形的,两边有竹帘摭挡住,里面铺满了稻草,是运筏人晚间睡觉休息的地方,我和弟弟看见里面没有人,就进去看了一下,哈,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是一套小人书《隋唐演义》,我和弟弟三步并做两步抱起来就往竹棚四下了张望了一下,呵,没看见人,于是我们也忘记自己来的目的了,在木筏上如履平地般跑了起来,到了河边,我想,可能那书的主人也会找来的,不如,我先在河边看会,等看完了我再放回原处去,这样,总不算偷吧,这样想着,于是我就心安理得的看起书来了。
看了一会儿,我觉得那套书大概太多了,好象大概有十来本,我根本就看不完,如果还掉了,我以后就没有机会看了,我有了占有这套书的念头,我的脚开始向家的方向挪动,不知不觉,边走边看,我已经到了家门口,我向小偷似的飞快地钻进自己的房间(我分了几本给弟弟看),我暗自决定等放完学如果那木筏还没有走远的话再物归原主。
下午上课,我一点心思也没有,就想着我得赶快把那几本小人书看完,好不容易熬得放了学,我又开始欣赏起了小人书,不过,我看得再快也没有看完,好像还剩七本没有看完,但是那个偷的感觉,让我又觉得内心不安,傍晚,我再次来到了河边,那木筏好象比我想象得要长得多,它依然还在河边,而我那破网也在河边睡大觉,今天竟然紧张得忘记了把捕鱼的工具收回家,要知道,那工具很可能会被别的捕鱼孩子偷走的,责备了一番自己的大意,我又暗自庆幸它们没有被偷走,刚准备收网走人时,忽然,木筏的竹棚里走来一个中年人,他拿着二个盆,好像是淘米准备做饭了,我心虚想溜,但是被他叫住了:
“你好,小朋友,你是在这里钓鱼的吧?”
“这里好象鱼很多,你今天一大早就在这里抓鱼是不是,这网都在这搁了很久了。”
“嗯,我是在这抓鱼。”
“收获不小吧?”
“还行,不算多。”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可能也指别的收获,我在想,莫非那是他的小人书。
“小朋友,你们家有书看吗,我在这放木排,没事干,也没有什么书看了,我有一套《隋唐演义》和你交换看,怎样?”
我一听,一愣,那书明明不是在我这吗,他······
那人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似的说:“小朋友,那套书是你拿走的吧,其实,我已经看完了,我只是无聊才买了这套书,我们在这等装车,车子大概要明天才会来装运,不知道你家里有什么宝贝好书,让我看看,好打发时间?”
“我们家有《霍元甲》,还有《追捕》,还有《西游记》······”我知道孩子的心思无论如何是瞒不过大人的眼睛的,于是我也不想再撒谎了,如数家珍般报出了我们家的那些最好的小人书名。
“那给我看套《霍元甲》吧,我没有看这电视,听说非常好看。”
“好,我这就去给你拿,但是你要答应我,你的那套书我要等明天早上再还给你,我的,你也要还给我,《霍元甲》是我最喜欢的小人书。”
大人就是大人,很是爽快,看着他点头,笑容里满是亲切,一点责怪我的意思都没有,我飞也似地跑回家拿书去了。
到了晚上,我们家出奇地安静,我和弟弟都在埋头看书,一点声音也没有,终于在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看完了这些书,晚上做梦全是什么程咬金啊,秦琼啊,朱元霸啊等等,我也不知自己梦中在穿插什么角色,总之和英雄在一起厮浑的梦,一定很过瘾。
早晨,我抱着一大堆书,跑到河边,可是河水清悠悠,什么也没有了,河里边只有欢跳的鱼儿在向我吐泡泡,好象在说:“你失约了,你书没有还给人家!”
我好懊恼,心想,我又不是故意失约的,我哪知道他大清早会不见踪影呢,不是说明天装车的吗,再说,我也还有一套《霍元甲》在他那呢,还说不准谁要谁的书呢。我一边寻思,一边踢着脚下的石子,满脸的不开心。途中碰到妈妈,只见她抱了一堆书说:“今天早晨我在河边浇菜时,碰到个叔叔说是还给你的,还有,他说,他的那套,就送给你了,不用还了。”我在奇怪他怎么会知道那是我妈,也许是我和妈妈长得太象吧。
我不知道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觉得好幸运,凭空的多了一套好书,而自己珍爱的《霍元甲》又失而复得,这样的好事如果天天有该多好啊。
我赶紧回家要向弟弟汇报这个好消息,因为他还没有看完,我是逼着他把书给拿来的,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坐在家里,慢慢悠悠地看了。
但是我却怎么也回忆不起,那人当时的摸样,因为那天我害怕那人说我偷书,胆胆怯怯地,说话给书都不太敢正眼瞧人家,现在倒好,别人送了一套好书,却连模样也不记得,只记得那声音有些山里人特有的味,嗯,确切的说,有如蜀水河般清醇的声音,哎,虽然时隔很久了,我依然记得那声音,那木筏!


住在寨下,应该说最大好处,一是游泳,二是上学,其它的优点也没有很多,哦,还有,很利于看病,最不方便的倒是看电影了。
游泳前面以前已经说过了,上学也说过了,现在应该说说看病了。
八一八的医院,应该说是比较干净的,我到过县城的医院,虽然比八一八的医院大一些,但是那卫生状况可不敢恭唯,而我们自己的医院却是犹如个小花园,它坐落在蜀水河边的一个小山包的后面,四周用青砖砌了娄空的花墙,穿插着在墙边种了些桂花,每到八月时分,医院便飘散着淡淡地桂香。一进门的右边是门诊室和挂号大厅,正对面便是住院病房,左右二边的空余地面有些花坛,花坛里面最多的是月季和蝴蝶花,好象是可以做药用的。门诊大厅与住院病房的衔接处是照X光和B超的地方,还有一些化验的地方。而医院四边是一排排的柚子树,也零星种有一些桔子树和别的不知名的药材树。每当春夏之交时,便会有浓浓的桔子花香沁人心脾,不时有蝴蝶在那儿翩翩起舞,山边的小鸟也在这花园般的医院雀跃,伴着蜀水河的潺潺流水,没有来过八一八医院的人还以为是个疗养院呢!那柚子听说是沙甜柚,但我却从来没有尝过,一是我家离那有些距离,二是医院的柚子总觉得会带股药味,所以我从来不摘医院的柚子吃,在那靠着蜀水河的边上,也是靠近医院厕所的旁边有一个与地面差不多齐高的房子,有一次顽皮,见那屋子矮,如战壕一般在地面的下方,而且结构也和别的房子不一样,屋旁有几根粗粗的有点象锅炉房样的管子,觉得很奇怪,便跑下去看个究竟,很不幸地是,我还没进到里面便吓得跑了出来,竟然发现是个太平间,哎,我那时真是有点皮过头了,连太平间也敢闯,后来,只要是往那个方向走,我都有点心惊肉跳,尽量绕开那所房子。
八一八的医生,在我小时候看来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穿着天使般的白大褂,很少看见戴帽子,也不知那时候有没有帽子,他们起初大部份是些支内的医生和护士,医术和经验都很足,后来又陆续分配了些很年轻的附近县市的护士、医生,虽然人年轻漂亮,不过,他们除了年青以外,其它都不如那些支内的医生护士。
不知为什么,可能那时候衣服的款式、颜色、花样较少吧,每每看见那些穿白大褂的护士,我总觉得非常的漂亮,白白地衣服衬得她们的皮肤个个都是那样娇嫩可人,而那些男医生也显得非常的圣洁。
小时候经常生病,对那的医生护士应该是熟悉得不得了,印象中常常是爸爸背着我,先来到挂号室,我便扒在墙边掂起脚往里看,在那里面有比我个子还高的橱窗里放着整整齐齐的病历,黄黄的,好象只要是职工都有个病历档案在那里。记得好象最初是陈院长的夫人在那挂号,那个院长的夫人非常漂亮,个子较高,脸型长长的,是个上海人,每次看见她时总觉得特别舒服,她嘴角边时常挂着一点也不伪装的微笑,也就是亲切亲切再亲切的那种微笑,我无法形容那种自然甜美的微笑,但我能感悟她对病人的亲切和热心,每次看到我这个小病号,她都略带怜悯的说:“哦,小家伙,又生病了,怪可怜的,天冷可要多穿点衣服啊,不要总弄得感冒啊。”但是到了后来,挂号的人就不太固定了,总是有些更动。学校刘校长的夫人好象发药兼挂号,感觉中她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总带着她独有的家乡口音,说话做事总有些急匆匆的感觉,而且那嗓音让我觉得和医院特别不协调,要知道医院的挂号大厅常挂有个大大地“静”字,而她那嗓门能让你听后还感觉有回音,所以我还是喜欢那些上海阿姨和医生,他们的话语间常常带有浓浓的吴音,也就是上海腔的尾音,听起来比较温柔,常常在他们连哄带骗的吴音中给猛的扎了一针,等到发现时已经是欲哭无泪,他们还会拿着那针管说:“说了很快地,不疼吧,瞧,这不打完了,打了针,病就会好的,来,给你个药盒子玩。”于是我常常拿着那个药盒离开了医院。
八一八的医院医生很多是多功能的,他们值班时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有拍X光的、照B超的也会值班看病。我对最初的那个陈院长有着较深的印象,他一看就是那种属于有着较深学问的人,嘴角上留着撮胡子,不高不矮的个子,眉毛特别的粗浓,声音非常的宏亮,看见他让我有些畏惧,因为每每看见有胡子的人总有些害怕,可能是那时候抗战片子看多了,里面的日本鬼子总有那么撮小胡子,但他的医术却是挺好的,那时候在他的带领下,全院几乎收治了犯各种各样病的职工,记得有一回爸爸住院,我去看望,那里面的医生就说:“小孩子不要到处乱跑,那是传染病区”,而后我又看见又一个拄着拐杖的打着石膏的病人出来,更有刚刚出生的小孩的哇哇哭声,那时候的病房常常会满,可能是那会儿厂区的人较多,而厂里医院的医生医术还算高明,一般的病都能治好,其中不少八一八的孩子都是在那待产出生的呢。可是到后来那些年纪稍大点医生都退休了,一些上海医生也调回上海去了,只剩下些较年轻的医生、护士了,医院的病房也没有往常人多了,常常是转到外面的医院去治疗。
在我那个年代看病,药品并不繁多,用来用去就那几种药,医生给我开的药,我都能背出来了,我常常是一感冒就支气管发炎,于是医生便开些四环素、安茶碱、菲那根、止咳糖浆等,有时候病情重点就会打青霉素、链霉素、庆大毒素之类的药。那青霉素每次打都要做皮试,护士拿皮管给你手腕一扎紧,再用那种青青的小针管给你那手腕上挑起一丁点的皮肉,然后便是一阵刺疼,接着坐等十五分钟左右,等到那小手腕上冒出一个小红包包,犹如给蚊子叮了一般就可以注射青霉素了,打针的医生很尽责,如果打完青霉素你没有坐满他们规定的时间你是绝对不可以走的。注射室里常常是二个护士,那儿打针的登子特别的高,还有些台阶呢,我小时候常常是不用坐那登子的,而是被爸爸反扒在腿上,然后把我的小腿一夹,裤子一扒,护士便飞快地扎了下去,每次打针哭了以后,我就能得到诸如药盒、没有针管的注射器之类的玩物。但是后来大了些,便有些不好意思了,每次尽量压抑住想哭的情绪,但眼睛却总有点湿润,可能还是忍不住想哭,而且还得坐在那有二三个台阶的高登子上,护士们也不再哄我了,看病时我常常是自己跑去的,因为那的医生我非常熟悉了,“久病成良医”,也不用医生看,我自己会非常机械地报出药名,我尽量报那四环素吃,而别的药我常常会骗医生说家里还有不用开,因为那些药只有四环素最好吃,有一层黄黄的糖衣片,一点也不苦,可就是那四环素,让我今天有了连牙虫也不敢沾染的四环素牙,可见其药效有多大。后来,我特意咨询过牙科的医生,问这四环素牙有没有办法根治,答案是,已经深入牙釉,根本无法根治。于是,现在我常常不敢开怀大笑,要知道那口牙齿实在是让人不敢恭唯。
有一次医院初进感冒胶囊,我拿着那好看的胶囊觉得那哪是药啊,简直就是一粒粒诱人的糖,看着那用透明塑料包装的,红白相间的胶囊,我想象着那味道一定比四黄素还要甜,便迫不及待地想打开,可看了半天却觉得无从下手,我翻过背面,全是锡纸,再翻过来就是一粒粒的胶囊,我用手指在正面使劲地抠想把那塑料弄破,结果胶囊在透明的塑料里变了形,却仍然没有取出来,我只好翻到背面,用指甲一抠,呵,出来了,再接着我又不加思索的把药扳成二半,有些粉末状的五颜六色的药粉蹦了出来,于是我赶紧往嘴里倒,那药一沾舌头,我便“哇”的一声,全吐了,后来哥哥在旁边看见了,说:“这药应是连壳一起吃的,不用剥开的”。可是我以前吃的药是没有这样包装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层包在外面的囊是可以吃的,而且那好看的药,却是如此的苦,不过,我那回却是自讨苦吃,后来事实证明连着透明的囊吃是一点也不苦的。以前吃的药,都是从药房那种深棕色的大药瓶中倒出来,然后医生便用一张一张的裁好的小白纸包给病人,上面写好一天几次,几粒,象那种四黄素,多放二天便会糖衣和纸粘在一块,不好吃了;那种没有糖衣的药,一沾嘴便苦得想吐,再后来便有越来越多的和感冒胶囊一样包装的药了,不过,药名也是稀奇古怪了,可能同样的一种药会有很多种叫法,而我长大之后吃药看病都很少了,只是看到报纸上的药价虚高,什么医生拿红包回扣之类的话题,可那时候在我们的八一八是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的,那里的医生和八一八人都如蜀水河般清纯,而那些装在深棕色瓶子里的药,虽然苦些,包装差些,却一样治好了八一八的许多病人,现在那些漂亮的药,好听的药名,除了鼓了药商、厂家、医生的腰包,可没见给老百姓什么别的实惠!
小时候,那生病时吃的药和现在的胶囊一比总觉得设计得不太人性化,多是苦得让人反胃的,于是爸爸总是会给我买些一分钱二粒的水果糖,让我吃完药能堵住小嘴不再呕吐,每当弟弟看到我吃糖便会说爸爸搞特权,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爸妈常常听医生说什么吃了好便千方百计去弄一些给我吃,比如说蛤盖,那是一种象壁虎一样的东西,还有猫头鹰,蛇等等,记得有一回,有一位苗医,用什么土方,说是能治,弄得我一颈一脖的拔火罐印,还用灯芯草在脖子颈边扎,说是有什么穴位扎了能根治,但事实上我的气管炎是在发育的时候自然而然好的,在这之前,无论父母怎么给我寻医用药,都无济于事,反正我好象是爸妈前世的冤孽,总在向爸妈不停地“索取”。常常是半夜忽然发烧,爸爸便用大衣裹着我,打着电筒去看病,而那时候的我特别温顺、乖巧。爸妈说,也只有生病时才是我最老实的时候,手脚可能会有所停吧,现在看到女儿即使是在看电视时手脚也会不由自主地摄衣服边或用手绞别的什么东西,我想可能是像我吧。妈妈常常说我:“你生病时是一条虫,不生病是时就是条龙。叫你不要天热去外面抓鱼捕蜻蜓,你就不听,看啊,疯得一身汗,风一吹就生病了不是,哎,真是的,你这孩子不听话,就是要打针。”
我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边在吃着最后一粒药,那边就寻思着是不是要去山上摘映山红或拔竹笋了,反正我小时候,根本就不象个女孩子,纯粹是一个“野丫头”。很搞笑的是,我这“野丫头”还会存药,如果我感觉自己病情好些了,就会把剩下的针剂藏起来,而剩下的药也用小纸包好放入小药瓶,等到我下次生病时,就拿出来吃,只要不发霉,我就吃,而那针剂我只试着拿出来一次,便给护士没收了,她们说:“不同批次的青霉素都要做皮试,人的体质是有变化的,你这次不过敏,不代表你下次不过敏。”而我本来是希望用老青霉素应该不用再作那疼死人的皮试了,可惜我终究不是的医生,给否决了。到后来,我看病情好多了,干脆就把剩下的针剂给抛了,要知道,打针实在是太疼了,我情愿浪费这些针剂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屁股再遭皮肉之疼。这些秘密父母一直都不知道,不过,现在这个秘密可是一览无余了,各位,可要帮忙保密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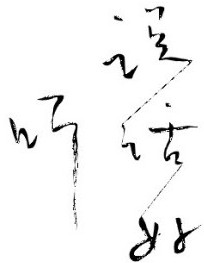















Copyright ©2006 - 2008 818的家园 |
管理员E-mail:818jy@163.com wdsyht@163.com |
悠悠三线情QQ群:43728877 818的家园QQ群:62568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