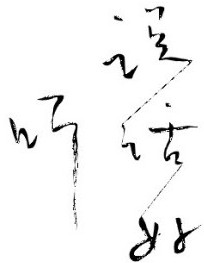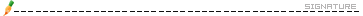得乐园
我们的中学时代在1972年早早划上了句号,之所以大部分同学没去县城继续学业,是因为即使你读了高中,即使你的成绩很好,但你也没有大学可读,当时强调在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所以生产劳动对年轻人来说是必不可少,那么,还是早点就业的好。
818厂把我们班级的30几位同学编为3个组,一个组在农场参加农业劳动,2个组下车间干活,半年一轮。每月由厂里发给生活费9元。厂里把我们的劳动称之为学工学农,现在想来真不合算啊,因为文革结束后,我们的这段学工学农的经历不计入工龄,哪怕插队也是算工龄的,而另一个事实是在1975年,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说三线厂的知识青年也要下农村锻炼,我的大部分同学还是去了农村,这样我们硬碰硬比实际工作减少了3年的工龄。但厂里的领导对此给予了些补偿,拨了一笔钱给下乡的同学修造了青年点,还给他们买了拖拉机,这是后话。
我所在的小组一开始就被安排到二车间学工,厂子里给我们发了工作服,是藏青色的,口袋上方有一排字:抓革命促生产,还发了解放鞋,我当时激动极了,虽然不算正式参加工作,但自以为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我被安排在202工房,成了一名操作工。这个工序就是把装满硝化棉的口袋放到脱水机里脱水,中间还要按定量注入酒精,(由专门的加料员操作)到时间后把硝化棉取出来,放到平板的手推车上,等下道工序来取用,劳动强度不算大,但要倒班。
车间在一道山沟里,溪水潺潺,林木苍翠,空暇时一卷在手,陶然自得,伊然世外桃源!不觉之间,中午到了,食堂的阿姨们用小四轮送菜来了(饭是自己蒸的),胃口好极了!中班下班路上,皓月当空,繁星闪烁,深夜山野里四处静悄悄,树木也不在沙沙响。到家了,“推门瞬心快,明日必天晴。”。这种意境现在到哪去找?就是夜班辛苦一些,临睡时把闹钟开到11点半,铃声一响,睡眼惺忪地起床,登上厂子里的大巴士,晃晃悠悠到了工房,下半夜还不免睡意朦胧,可到了清晨,林子里鸟儿歌唱,昆虫呢哝,杲杲的太阳升到林梢,又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白天!
在车间的劳动中,我们结识了不少青年职工,上海来的老三届很有绅士风度,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蚊帐里挂着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涤卡中山装,这在当时是很好的衣服了,只有上海才能买到,而且要纺织专用券的。我还认识了一位福建籍的复员军人,他的妻子在家乡,有一次他犹豫地拿出妻子的照片给我看,就像拿出不轻易示人的珍宝那样,脸上浮现出十分思念的神情。
农场的劳动也很有意思,“寻梦,撑一杆长篙,向青草更深处漫朔”,诗人徐志摩这样写道,我们就曾感受这样的意境。清晨,太阳初照梅陂河上,撑着一叶小舟,到河心岛上去拓荒种地,同学少年,春华秋实,既感觉播种的艰辛,又享受到收获的喜悦。
建厂之初,为了备战和防空的需要,不少工房都建在山洞里的,但山洞潮湿,通风不好,是不适合生产的,因此后来进行了出洞的建设项目,建新工房,需要重建管道系统,工程量很大,我们这些学工学农的青年有两个组被抽调到机修车间,参加出洞的工程,男同学学做冷铆工,女同学学电焊,冷铆是技术工种,但劳动强度很大,而且需要爬高落低,那时我们正值少年十五二十时,高空作业,全无畏惧,比方:新工房上方有一道工字钢,横贯十几米,高度有三个人那样高,师傅在那端说,把焊枪拿过来。我们就拿着焊枪,在没系保险带没有扶手的情况下,从工字钢的这头走到那头。我印象中冷铆工技术难度最大的是放样,就是把图纸按照比例的要求放大到铁板上,然后用气割枪割去多余的部分,大的规则的管道可以用卷板机卷制,小的不规则的部分则用锤子捶打而成,师傅用小榔头点,我们就用大锤敲打。师傅点到哪里,我们就锤到哪里,管道与管道的接头部分则用焊枪焊接,焊接前要用“退拔头”,把管道高出的部分压下去,才能焊接服帖,分工不是绝对的,有时我们也拿起焊枪点焊。当时的工人真是不计报酬,不计上班下班,不怕艰难困苦,他们豪迈地说: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
记得有一次五车间的车床工房失火。厂里出动了不少职工进行修复,铆工负责翻修屋顶,用石棉瓦铺在屋顶,然后用长螺丝固定,钳工则把烟火熏黑的车床擦亮,校正误差,还用锉刀把车床锉出好看的花纹,只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把工房修复如新,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参加了这次劳动,心中很有感慨,我们也为818厂的建设出过力,淌过汗,流过血。
许多年代过去了,命运曲折和深邃的旋律把我们引到了四面八方,可想起当年学工学农的情景,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那是我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序曲,劳动给了我们愉悦的精神,劳动给了我们健康的体魄,劳动使我们懂得不少做人的道理,劳动让我们心里踏实。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留恋”(普希金)。 劳动真好!
谨以此文献给我当时的师傅们和一起参加学工学农的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