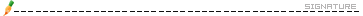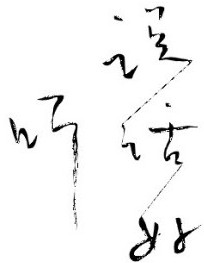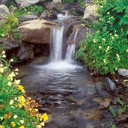春天是个流感流脑肝炎心血管病高发季节,我怀疑这一切和春天的风有关,春天的风是邪风,它的成分包括法国梧桐籽絮和杨柳絮,外加由于环境的破坏导致肆虐的风沙颗粒、以及你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病毒。如果你注意观察,你就会发现那些本来好好地走在街上的人突然要眯着眼皱着眉头,侧过身子甚至背过身子跓足不前,这就是风的杰作了,它只顾自己乱动乱闯,随手抓起一把杂质就往行人的脸上扑,害得那些走在街道上的人不自觉地偏离了方向,走进了非机动车道。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人往往在非机动车道上一个急刹,“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啊”骑行者们的咒骂声伴着尖厉刺耳的刹车声此起彼服地溶合在潮汐般的市声中。街道马路上经常有一些不太牢固的广告牌停车牌在风中倒下或者像生了脚一样地逃离开去。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电视新闻里,有好几次播放了险象环生的高空坠物事件。还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了街边码放得整整齐齐的自行车在春风的恶作剧下,完成了一次多米诺骨牌试验。诸如此类的春我真不知道人们有什么理由喜欢春天的风。
更可恶的是春天的这股邪风还害得许多人患上了面瘫,祥庆里七十八岁的郑伯和我们街口漂亮的报亭西施小梅不幸被这股邪风吹成了面瘫。郑伯是早上八点准备装上假牙吃早饭的时候发现的,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左颊的肌肉无法牵动,似乎有种不听支配的麻木感,于是他叫来老伴儿,想请她帮忙看一下,结果就发现自己的半边脸面已经罢工了。而小梅则是一大清早洗漱时发现的。她发现自己刷牙时涮口水总是不听使唤地从右侧嘴角边漏出来,感觉不对劲,再一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已经口眼歪斜的可怕情景,这对于爱美的年轻女孩来说不啻虚是个沉重的打击。
医生我会不会好起来呀?小梅在医院里焦急地询问主治医生。而医生的话却让她的心头更为焦虑。如果你注意休息配合我们治疗的话,应该会恢复的,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后遗症。医生的话听上去千篇一律模棱两可,我们知道医生向来擅长用这类外交辞令来对付那些喋喋不休的病人的,他们总是在一定适度上给患者以希望,但也同时阐明了事态的严重性。什么叫应该会恢复?那就是说还不一定喽?后遗症是怎么样的?小梅现在说话严重漏风,但她却希望医生给自己一个确切的答复,因此她冲着医生连珠炮似地发出一连串模糊的疑问句(因为面神经瘫痪导致了她说话时嘴角严重漏风)。医生却不再理会她,只顾埋头在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着草书,先去付费,然后到肌注室打针,每周三下午一次针炙按摩,下一个。医生最后说。
如果你要是觉得医生的这种表现是因为太不懂得怜香惜玉关爱民生,是医德伦丧的话那你就错了,医生的这种表现完全是出于一种见多识广见怪不怪的正常表现,在他们看来,除了不治之症外就没有什么天大的事,为了医治更多的病人,他们不可能做到耐心细致地向每一位病患做一个病理说明。小梅回头看到候症室里密密麻麻的病人时就忍住了想继续追问下去的念头,何况医生已经在催促下一个就症者了。
就在小梅奔走于医院进行打针吃药针灸按摩多管齐下治疗的时候,郑伯也在用土办法医治他的面瘫,郑伯的老伴广东阿婆充当了他的主治医生,那段日子庆祥里附近的许多居民和我一样,看见她蹲守在菜场卖鳝鱼的炳彪摊位前,每逢炳彪为顾客杀完黄鳝,她立刻操着广东口音叫住炳彪,不要冲不要冲。她阻止准备用清水冲洗案板的炳彪,敏捷地伸手到黄鳝的行刑台上抹了抹充满腥气的新鲜黄鳝血,然后一把拉过郑伯,在郑伯没有患病的一侧面孔上涂抹起来。郑伯很听话地任由广东阿婆在自己脸上操作着,他也很想对那些因好奇而跓足观望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打声招呼,却想不出说什么好,只能尴尬地笑笑,这一笑倒令郑伯的嘴歪斜得更厉害,加上涂了半边的脸血赤糊拉的,显得既滑稽可笑又有点恐怖。更为荒唐的是,广东阿婆还从樟木箱底翻出当年嫁过来时父母祖传的陪嫁礼品,一枚黄金戒指,她把金戒指掰开,加工成了一只金钩子,拴上红丝线,将线套在郑伯的耳朵上,另一端的金钩则钩在郑伯下垂的左嘴角上。
拉一拉就好了,歪掉的嘴会吊回来的,我阿妈就曾经给村里人看好过这种毛病。广东阿婆对好奇的领居说。这是不是叫作吊金龟婿呀?同一个院里以嘴坏出名的阿六头打趣地说。不过广东阿婆并没有听到他的说话,不出一个月就会好的,你们信不信。阿婆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切,阿婆这是瞎胡闹,太不科学了,有病要看医生,这样做分明是在搞封建迷信。我们老师说,不能讳疾忌医,这样会耽误病情。初中生大建的话说出了我想要说的心底话。当时许多祥庆里的居民都和大建想得一样。稍具科学知识的人们普遍认为广东阿婆这种行为完全是毫无道理的迷信行为,郑伯应该和小梅一样,到医院去看病。
三个月后,我家附近的两位面瘫病患者郑伯和小梅,一个恢复了正常,一个却留下了后遗症。出人意料的是,完全恢复正常的居然是郑伯,而美丽的报亭西施小梅,却留下了后遗症,虽然外表看起来,小梅仍和以往一样妩媚动人,但只要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她笑起来的时候总爱以手掩嘴,那是为了遮掩她一笑就显得有些略微右斜的嘴角。当然这不妨碍她的美貌,相反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动作在小梅众多的追求者中显得更添几分神秘的美感和韵味。她有那种古代大家闺秀才具备的娇羞,我就喜欢看她笑不露齿的样子。一年后在小梅的婚宴上,我们听到幸福的新郎小齐是这样向嘉宾们坦白自己爱意萌动的缘由的。这无疑是面瘫给小梅带来的意外收获。
许多人对郑伯的完全恢复觉得不可思议,郑伯笑起来声音爽朗而显得和蔼儒雅,不论从何种角度观察,他的嘴角弧线都显得异常完美,没人怀疑郑伯年轻时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帅哥。同样是被春天的邪风吹歪的嘴,为什么积极而科学的治疗没能使小梅完全恢复,相反用这土法医治的郑伯却完全恢复了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和当初那几位崇尚科学邻居的一样,对广东阿婆的医治手法感到不可思议。直到多年后借助网络查阅到一段文字才恍然大悟,资料上写道:鳝鱼血治疗面瘫,《世医得效方》以“大鳝鱼一条,以针刺头上血,左斜涂右,右斜涂左,以平正即洗去”的治法,说明涂鳝鱼血是自古以来中医治疗面瘫的方法之一。一般认为:鳝鱼血活血搜风通络,涂于局部,干燥后,能牵引面部肌群,刺激神经,促进瘫痪肌恢复功能。
这样看来,广东阿婆貌似毫无科学道理的偏方土法还是有些科学道理的,以至于我回想起来,她用金戒指钩嘴治疗面瘫也是一招起到类似石膏固定骨折病人的效果的,乃是不以常法制胜奇招,广东阿婆后来成为祥庆里一带著名的面瘫医师,她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将那些被邪风吹歪嘴的面瘫病患者的嘴角拉回到正常位置。她从来不收求医者的钱,出于感激,被她医好的患者总是在逢年过节时送给她不少火腿香肠之类的东西。在患者们看来,能治好这种病,出这么点血算什么?
可我们祥庆里也有小气的人,比如被称之为葛郎台的葛仲达,这些年做股票发了小财还那么抠门,他至今还在抽那种五元钱一包的劳动牌香烟。人人都知道节俭是美德,可是“葛郎台”只知道从别的邻居手中接过好香烟抽,自己却连一根最差的香烟也没有发给别人过,以至于后来熟悉他的人远远地见了他就赶紧搯灭了手中没抽完的烟,他们不甘心却又拉不下面子,所以宁可浪费大半支香烟也不愿再肯递一支烟给这个抠门到家的“葛郎台”。也有些拉得下面子的人,就算迎面碰见了也照抽不误,楞是不给“葛郎台”递烟。
没见过这种人,他见我在抽烟,就恬着个脸伸手来讨,我就故意不给他抽,看他怎么样,嘿嘿,他可倒好,见我没有给他烟抽的意思,就从自己口袋里掏了包软壳中华来,当我面拆开,嘴里还说什么这种烟还不如劳动牌好抽,你说气不气人。这一次阿六头气愤的诉说引来了大家的共鸣。就是这么一个出了名小气的人,前年的春天也患上了面瘫,那天“葛郎台”从证券所出来,嘴上叼的香烟忽然从嘴角滑落,起先他没在意,从地上拾起后继续吸,乖乖,漏风了,任凭他怎么努力,却怎么样也吸不动那只快要灭了的香烟。“葛郎台”一侧嘴角并拢着而另一侧却微张着合不拢。歪斜了嘴的“葛郎台”还要抽烟,烟从一侧嘴角吸进去又不断地从另一侧嘴角漏出去。
你这样抽烟不是浪费嘛,快去找广东阿婆看一下吧。阿六头见了“葛郎台”这个样子想笑又不敢笑,只好表示一下关心。没事的,这种小毛病我也会治的,哪用得着劳烦她。葛郎台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
他会治?我看他心里头担心让别人看病要付出的那点好处。阿六头这种想法得到了街坊领里的普遍认同。“葛郎台”最终为自己不舍得付出这点小利付出了代价,他自以为掌握了医治面瘫的偏方,却没有没有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也去炳彪的鳝鱼摊前讨来黄鳝血涂抹,也用老婆的金戒指来吊嘴角。最终“葛郎台”的嘴能合拢了,面部神经也恢复了自如的支配功能,他又可以正常抽烟了。可是从外观上来看,他留下了比小梅更为严重的后遗症,即使是他不说话不发笑,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嘴角严重向左歪斜。当初他患病的一侧明明是在右侧,照理嘴角应该向右侧斜才对呀,怎么反而往左侧歪过来了呢?祥庆里的老中医郭坤乾一语道破天机:鳝鱼固然可搜风通络,牵引面部肌群,然不可矫枉过正也!他这样摇头晃脑地咬文嚼字后许多人仍然不太明白,最后由我向大家做了白话翻译,我告诉大家说,“葛郎台”就是嘴角拉过头了,结果另外一边的嘴就歪了。
也许是经过这么一场面瘫病的洗礼,“葛郎台”有所触动,庆祥里的居民们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葛郎台”小气的毛病有所改观,现在他见了谁都主动发烟,尽管还是廉价的劳动牌香烟,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了。最令人有目共睹的一次就是在去年春节前广东阿婆过世的时候,“葛郎台”亲自登门送去了一对花圈,除此之外还有一对锦锻的被面。这倒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啧啧称奇的街坊议论纷纷,谁也猜不透个中原缘,当然我也猜不透,这事不像鳝鱼血可治面瘫病那样,是有据可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