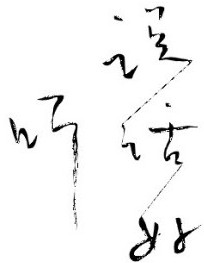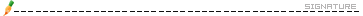二零零八年七月上旬,一种不祥的预感每时每刻都在缠绕着我,我正在忍受和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折磨与即将失去亲人的痛苦煎熬。每当手机铃声响起,我便会紧张地看看显示屏的区号,是不是从上海打来的。七月七日中午,这种不安终于变成了现实。妈妈从上海家里打来电话,她哽咽的语调携永着母亲与父亲五十年历经风雨的沧桑。“阿三:你爸爸快不行了,你有时间就回趟上海,见你爸爸最后一面吧”。
放下电话,我心为之一沉,父亲健康每况愈下我是有思想准备的,父亲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我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送他走完他人生的最后历程。但是我没有赶上,直到今天想起,我都在为这种遗憾而悔恨。记得那天,天气闷热,简直可以让人窒息,当我稍作整理,匆匆忙忙挤上开往上海的列车时,南昌的天空下起了雨。
正赶上学校放假,车上人很多也很拥挤,声音嘈杂,使我感到异常烦躁和不安。在焦虑、急切、烦燥中列车终于缓缓滑动起来,车轮撞击着铁轨,雨水扑打着车窗,列车员广播着乘车注意事项,随车小贩夹着方言在叫卖,还有婴儿渴求母乳的哭喊,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昏沉中望着车顶上的那几盏灯,眼前浮现着父亲趟在床上,戴着老花眼镜,手捧一本外语书在认真朗读的情景。八十岁高龄的他在朗读时发音虽然不太标准,时儿还夹着宁波口音,我们听不懂,不知道外国人是否能听懂?但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光仍在向我们展示着他孜孜不倦坚持学习的傍样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知识的追求是多么难能可贵。
父亲是个孝子,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孩儿。他在家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妹妹,爷爷去世得早,奶奶早年守寡,含辛茹苦的带着几个孩子,父亲为了减少家里的生活压力,八岁就给村里的有钱人家放牛,十三岁到上海做学徒,白天做工,晚上还去私塾学文化。大伯、二伯结婚成了家,大姑、小姑和奶奶还在宁波奉化老家,供养姑姑、奶奶的家庭负担就全部落到了父亲一个人身上。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连年的战争之中,但是父亲在上海的工作相对较为稳定,他老实、本份的秉性深得老板的亲睐。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老板在逃离上海时给父亲结清了工资,父亲送钱回宁波老家,在回上海的路上被地方上的和平军抓了壮丁,关进了一家为固守上海的汤恩伯军队做被服的工厂,不到一星期,上海外围解放,父亲所在的被服厂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军军需部被服厂,父亲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军需被服厂的战士,为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的解放军战士做被服,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才转入一家公私合营的橡胶厂工作。
父亲是个循规蹈矩与事无争的人,是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wg初期,由于对zfp破坏生产,停产闹革命的错误行为说了几句批评的话就被zfp装进麻袋一顿暴打,全身上下一片青紫浑身是伤。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背上那只大头皮鞋的青紫印特别剌眼,直到今天,它都象一块盘石压在我心头不能释怀,因为我没能帮父亲找出留下这只罪恶鞋印的原凶是谁?那时,我家住在上海中山北路中兴村,每到星期六傍晚,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都会到公共汽车站去等父亲。一九六七年夏天的那个星期六,我们从傍晚等到深夜也没见到父亲的身影出现,没有等到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带给我们吃的油煎馒头和面包片。第二天下午,母亲才打听到父亲被人送进了上海市广慈医院。父亲是个老实人,怎么会遭遇如此劫难呢?是谁如此狠毒?为什么要对父下如此毒手?直到今天我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也许这就是当时混乱政治的一种特性吧。父亲在家休息了很久才去上班,但一到春天老伤复发,疼痛难忍。
父亲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党龄比哥哥的年龄还长。上世纪六十年代的wg时期,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一九六五年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一九六八年响应毛泽东参加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报名参加了支援三线建设。一九七O年的除夕,我们举家从上海迁到了江西省泰和县井冈山脚下一个山沟沟里。在即将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上海一眼,在孩时的记忆中,上海街道两边都贴着大字报和各种各样的标语,空旷的地方都挖了战壕。那时候,南边美国人在打越南。北面苏联人在中国的珍宝岛进行战争挑衅,西南边的印度与中国的邻土之争,当时的中国好象四面楚歌,大有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就会爆发了一样。当得知父亲带我们全家去一个能躲避战争,四面都是山,红军在那里打败了蒋匪军的井冈山脚下的地方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围在一起高兴得互相拍红了小手。
大伯、二伯、大姑、小姑都来上海北站送我们,父亲携着奶奶上了即将离开上海的列车,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我们一家七口人和一名列车员。虽然是在wg时期,我们在火车上还是得到了一份免费的晚餐。
一九七零年到了江西以后,由于江西的气候湿度太大,更容易引发伤疼,每每春季,父亲都要经受旧伤复发给他带来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后来,我们听当地老表说吃狗肉可以疗伤并且可以断根。七二年春节期间,我从山上拾回两只小野狗,当时一到晚上,老野狗就到我家附近叫个不停,大有不讨回小狗不罢休的气势,吓得我们一到晚上就紧闭大门,不敢再到屋外去了。
两只小狗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慢慢的长大了,跟父亲的感情特别的深,每天跟随父亲上下班,陪父亲去赶集买菜,父亲下班回家在菜地里忙着翻地,它们就在一旁蹲着,时儿在父亲跟前摇摇尾巴,时儿用舌头添添父亲鞋上的泥污。狗儿长大了,饭量也大了,那时候,人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粮食给狗吃啊。父亲就从工厂食堂的餐桌上捡一些骨头和饭渣回来喂养它们,狗长大了,我们准备先打掉其中的一只为父亲疗伤,但被父亲拒绝了,家里当时只要有人提起打狗的事,父亲就会说:“罪过,罪过”。
由于家属区养狗的人家太多以致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而且反映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有一天,厂里的广播里播放了保卫科的打狗通知,此时父亲仍在想方设法的保护那两只狗免遭劫难,当时父亲养狗的初衷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无奈大势所趋,父亲只好分两次将狗处理掉。吃了狗肉以后,父亲的老伤果然没有再复发,但是,从此以后,父亲再没养过狗,再也没有吃过狗肉。
父亲曾经连续五年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职工代表,他是国家正式干部编制,却在工人岗位上工作。面对自己被重新分配和安排的陌生工作,他任劳任怨,无私无悔,与世无争,默默无闻的工作到退休。
父亲一生很平凡,没有轰轰烈烈的骄人事迹,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分割的财产。但是,这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和睦与平静的生活。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不会溜须拍马,也从不知道怎么去求人开后门,以致我们一家人在山里生活工作时没有一个人分配到理想的工种。大家有的大家有,少数人有的他不争,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在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他希望我们继续他的革命理想,他想用他曾经每月只有七十四元的工资收入能养活我们一家人的事实来说服我们,而只字不提他自己每月仅留五元钱作为自己一个月生活费的艰难困苦。
父亲一生都很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他在一九四九年初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军,在军区后勤处工作,我见过华野的证明。但在父亲退休涉及到干部与工人待遇时,在父亲的档案中不见了那张证明,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虽然父亲退休时没能享受到干部待遇,这对他很不公平,但在我心目中,父亲就是参加过上海解放的战斗英雄。
父亲的节俭是一种傍样,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平凡中的伟大。然而,父亲一生辛劳,一生勤俭,直到他乘鹤西去,也没能在回到上海后再买下一个平方的栖身之地。他是现实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比之那些贪官污吏,父亲的伟大是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的。
一九九三年,父母随姐姐回了上海,工厂的现状也每况愈下,在改革的大潮中曾经倾注了一代人心血的江西庆江化工厂终于被涌起的污泥淹没了。二零零一年工厂开分流下岗,我自找出路只身一人先到南昌适应山外的生活和世界,在生活相对稳定后我回上海接父母亲来南昌住段日子。那时,父亲的身体还是蛮健康的,行动也方便自如,完全可以打理自己的生活和起居。只是一头白发使他显得有些老态。上了火车,父亲坐在卧铺的床沿上,他翻起几件衣服,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个手帕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手帕,里面都是些壹元、伍角、壹角的纸币。他仔仔细细一张一张的数着,前后数了两遍,觉得没错,然后又认真的用手帕将纸币包好放回内衣口袋里,抽出手后再在外面用力拍了几下,确认手帕包在身上后才躺下睡觉。当火车到了金华,他又重复着上车时的动作。根据医学理论分析,父亲可能已经患上了一种潜在的老年性疾病,因为此时,父亲动作和语言已经有童趣化的现象了。
父亲走了,他两袖清风的走了,他没在留下任何钱财,但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可供我们学习一辈子。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在父亲的追悼会上,父亲的一位友人在追忆父亲的怀念词中这样称赞到:“沈淼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正是他在平凡的工作中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用他的一生写下对党的忠诚和热爱,才使我们的党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如此的伟大和崇高......”。
回想起这一切,父亲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我的父亲永垂不朽。